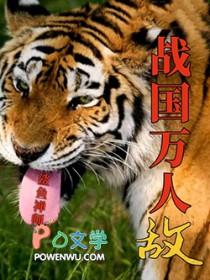山河小说>穿书农门粮满仓,我为权臣牵红线 > 第61章 灭鼠良方(第2页)
第61章 灭鼠良方(第2页)
檐下光影斜斜映在晏陌迟眉眼间,倒教人晃了神。
俄顷,他别过脸道:“纵使余承欢闹破天去,我断不会娶她。”
余巧巧心口发涩。
这红线怎的越牵越乱?
眼下也顾不得撮合,村中鼠患愈发猖獗。这两日死老鼠堆成小山,灶火整日不熄。
若是鼠群还未到顶,这般光景可怎生抵挡?
但愿新配的鼠药快些见效
外头七八个媳妇子正揉着蜜饵面。余巧巧点过数目,料着够用到明日晌午。
“婶子们劳累整日,且家去歇息罢。”
妇人们收拾家什陆续散去,独戚大嫂磨蹭着不走。
余巧巧知她心思,便将晏陌迟的话说了。
戚大嫂拍手笑道:“早说邓先生是个明白人!”
“到底是教书先生,最重礼义廉耻。”
“我家二旺跟着这般师傅,老身一百个放心!”
晏陌迟打廊下过,暗想这婆子前日叉腰骂街时,可不是这般说辞。
余巧巧扯着戚大嫂袖口低语几句。
“娘子放心,”戚大嫂笑出满脸褶子,“那猴崽子读书虽不成,这点机灵还是有的。”
送至院门口,暮色里飘来艾草烟气。
余巧巧望着远处山影,心头沉甸甸的压着事。
……
暮色透过窗棂斜斜洒在药碾上,老郎中枯瘦的手指骤然停住动作,颤声高呼:“巧巧!巧巧!速来!成了!”
余巧巧撩起布帘疾步踏入,青布裙裾扫过门槛:“这般快?”
老者沟壑纵横的面庞泛起红光,药杵在陶钵里敲出清脆声响:“你我师徒联手,岂有不成之理?”
昨日墙角那株蓖麻随风轻晃,叶缘锯齿如淬了毒的小刀。余巧巧采撷时便思忖,这毒物籽实经火焙炒竟能散出异香,若与夹竹桃汁相融,许是灭鼠良方。
此刻青石药碾中,焦褐色的蓖麻碎末与乳白浆液正泛着诡异光泽。老郎中捻须道:“单是混拌毒性平平,偏巧滴入数滴滚沸的陈醋炮制——”
话音未落,钵中药泥已腾起青烟,腥甜气息里裹着酸涩,“你瞧,这般相激相生,毒性何止倍增!”
“医者开方救人,讲究的是剂量分寸。”老者绕着药炉转圈,布鞋底蹭得青砖沙沙作响,“可这灭鼠的方子嘛——”浑浊眼瞳忽地晶亮如少年,“自然是见血封喉方显手段!”
余巧巧望着师父手舞足蹈的模样,唇角梨涡若隐若现:“师父教诲,徒儿谨记。”
檐下风铃叮咚,她望向渐暗的天际:“明日便与窦叔商议试药。”
“倒是治鼠疫的古方现成。”老郎中从樟木箱底抽出泛黄册页,“当年师祖在滇南”
“徒儿另有所求。”少女忽然屈膝行礼,话音被端着漆盘的康婶打断。
粟米饭蒸腾的热气里,腊肉与烘蛋的浓香漫过药香。
“再这般熬灯费油的,老鼠没除尽,人先成干尸了!”康婶将竹筷拍在案上,转头瞪着老郎中:“特别是你这把老骨头,今夜若再碰药碾——”
老者捧着南瓜汤嘿嘿直笑。
从前独居时,何曾听过这般裹着嗔怪的关怀?粗陶碗沿的热度不由得渗进掌心,恍惚又见三十年前师父拍桌训斥的光景。